
曾凭《寄生虫》横扫奥斯卡、用《素媛》《辩护人》叩击社会痛点的韩国电影,如今早已褪去“亚洲电影标杆”的光环。影院上座率跌至2004年以来最低,头部发行商供片量腰斩指南针股票,连朴赞郁、李沧东等名导的新作都难逃票房哑火或投资搁置的命运。“韩国电影不行了”的感慨背后,藏着的不仅是行业周期的波动,更是一场由内而外的“作茧自缚”。

存货清空后的创作真空,开启“三低”恶性循环。韩国电影的困境早在疫情期间便埋下伏笔,2021年起,市场就陷入“消耗存量”的被动状态——银幕上的作品多是疫情前已杀青的存货,真正的新创内容几近断层。当存货逐渐见底,创作端的乏力彻底暴露:题材上难以突破过往的社会批判、犯罪惊悚等固有框架,与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脱节;制作上则受制于投资收缩,陷入“低预算→低质量→低票房”的死循环。韩国电影委员会的数据显示,去年发行的37部商业电影中,仅10部能收回成本,这种惨淡的盈利状况让投资者愈发谨慎,进而压缩制作投入,形成恶性循环。曾经能诞生《釜山行》这类高概念佳作的土壤,如今连维持基本产量都成了难题,2025年头部公司年供片量已从40部锐减至不足20部。

票房造假丑闻的暴击,击碎行业信任基石。如果说创作乏力是慢性病,那么2023年曝光的票房造假事件便是致命一击。当年有323部电影被查出夸大票房,伪造票数高达267万张,影院、发行商等69名从业者卷入其中,后续更有调查将涉嫌造假的影片数量扩大至462部。这场丑闻彻底摧毁了市场的信任体系:观众不再相信票房数据的真实性,对“高票房推荐”产生本能质疑;投资者则因行业信誉崩塌而选择撤离,连李沧东筹备多年的《可能的爱情》都因拉不到投资而搁置。更严重的是,丑闻导致多个制作公司和导演的项目直接停摆,原本就脆弱的创作生态雪上加霜,其负面影响至今仍在发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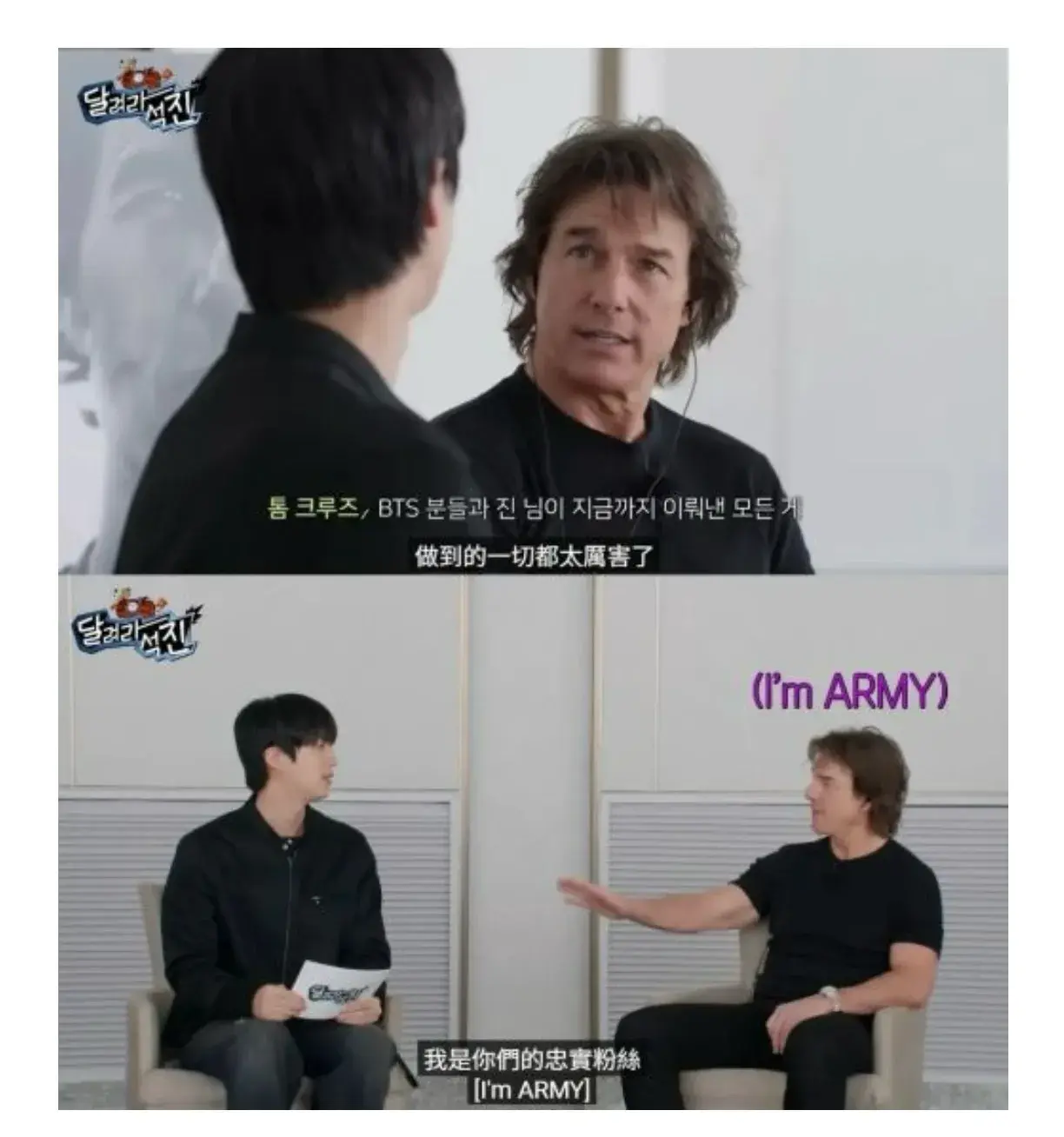
流媒体冲击与人才流失,加剧行业生态失衡。在内部问题凸显的同时,外部冲击更让韩国电影雪上加霜。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的崛起,不仅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——年轻人更愿意在手机上刷剧而非走进影院,更引发了严重的人才流失。顶级演员出演网剧的单集片酬可达10亿韩元,流媒体每年挖走的电影人才比例高达13%,连《K-Pop猎魔女团》这样的网络电影都能掀起人才迁移潮。忠武路的核心创作力量被分流,传统电影工业的造血能力持续衰退。尽管流媒体曾为韩国电影拓宽海外出口渠道,但当核心人才与观众注意力一同流失,影院端的颓势已难以逆转,2025年上半年甚至没有一部电影观影人次突破350万,全年总观影人数濒临跌破1亿大关。

如今的韩国电影,正陷入“老本吃尽、新力难生”的尴尬境地:影院靠重映《霸王别姬》等华语经典续命,政府不得不祭出1.08亿美元注资、发放观影优惠券等“CPR级”救市措施。从戛纳获奖到三大电影节零入围,从票房神话到造假丑闻,韩国电影的坠落轨迹警示着所有影视行业:创作力是核心生命力,而信任是行业存续的根基。当创作陷入惰性、行业失去诚信,再辉煌的过往也终究难抵“作茧自缚”的代价。韩国电影能否破局,或许要看其能否重新找回对内容的敬畏,在本土化与全球化、传统影院与流媒体之间找到新的平衡。
查查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